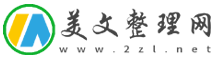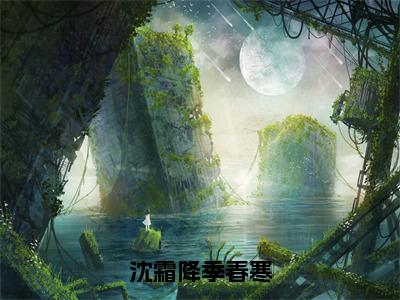孟韶欢(春水映桃花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孟韶欢春水映桃花_笔趣阁
 裴琨玉躬身行礼时, “轰”的又是一声闷雷落下,震的人耳廓发麻,旁人在这里站着, 纵然是在檐下, 也会被雨水浇透。 廊檐下的丫鬟和小厮、太监们早都被关回去了,特殊时期,不允许任何人胡乱走动,公主与裴大人要谈正事, 旁的人也不准偷听,这里没有任何人能瞧见。 而在任何人都没有瞧见的地方, 檐下其人端端正正的行着礼,不曾因雨因风而动上一下。 孟韶欢见他这般知礼,心底里那一颗悬着的巨石又轻了几分。 瞧瞧, 这才是世家公子,没有带着一群人将她抓起来,没有不由分说让她下狱, 没有翻出来旧账弄死她,而是给她行礼。 她面上便也带了些笑,与裴琨玉道:“裴大人请起。” 裴琨玉便缓缓站直了身子,又道:“裴某此行, 为南陈使臣病重之事而来, 有些话, 想要问一问公主。” 孟韶欢自然应下,她道:“请裴大人入书房详谈。” 不管裴琨玉问什么,她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。 说话间, 孟韶欢一步一退,引着裴琨玉进了书房间, 嬷嬷则老老实实的站在公主身后,跟着伺候——公主毕竟是公主,就算是搅和进了事端里,规矩也不能断,绝不可能放任公主与一外男相见。 书房内设了查案,其旁煮了一壶茶,煮沸的茶水冒出淡淡的嫩芽清香,孟韶欢落座后,管家嬷嬷亲手倒茶。 裴琨玉则询问了些关于宴会当日的一些细节,这些事,孟韶欢在暗夜无人的时候不知道揣摩了多少回,他问,她答,堪称对答如流。 问着问着,话题便落到了全贵公公的身上。 比如,全贵公公为什么逃走? 孟韶欢摇头,她不知道。 她说她不知道,裴琨玉便也不再追问,似是不管什么话,只要她说了,他就信一般,末了,还补了一句:“属下来之前颇有猜测,全贵公公无故而逃,想来都是他的过错,公主尚小,大概是被他蒙蔽了。” 多么中肯的话啊! 孟韶欢心里一喜,还没来得及说话,一旁的嬷嬷已经忙不迭的点上头了。 没错,都是全贵那老不死的狗东西的错,跟他们公主府可没什么关系,谁知道这个狗东西做什么失心疯,竟然敢谋杀南陈使臣,错可都是他的,莫要牵连到他们旁人。 而裴琨玉似乎没察觉到太平公主与这位老奴的心之所想,他端着手中的杯盏,不曾饮,只静静地听着她们的话,偶尔回上一句,处处细致,似是都是为她们好。 孟韶欢心上的大石头越来越轻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他不看她的面,似乎不好奇她面纱下的脸,不为难她,不提什么假公主,像是已经浑然忘了过去的事,只一门心思来办这个案,办完了,他们就该走了。 到时候,公主还是公主,就算是南陈的婚事不成,以后也可以找别的婚事嘛,他们日后大可以不再见面,京城这么大,他们躲得开的。 孟韶欢就抱着这样天真的念头,一句句回应他的话,只盼望着万事皆休,日后和平度日。 等到最后一句话问完,裴琨玉便起身,道:“今日多有叨扰,裴某告退。” 裴琨玉要走,嬷嬷便匆忙放下手中杯盏,起身去外面准备拿油纸伞,她一起身离开,书房中便只剩下了两个人。 孟韶欢正站起来。 这茶案矮,人跪坐在其后的蒲团上,为了姿态好看,都要跪的端端正正,时间一长,腿脚便酥麻,起身的时候最为艰难。 她站起来时还问道:“这公主府,什么时候能解封?” 既然罪责都在全贵公公的身上,这公主府也该得来一个清白了吧? 可裴琨玉没有回话。 孟韶欢抬起头时,便看见裴琨玉站在原地,黑漆漆的眼眸里看不到一点情绪,正定定地望着她,绯色的官袍被仅剩的烛火光芒一照,便映照出如血一样的颜色来。 刚才还霁月风光,不肯看她的人好似在缓慢地撕下自己的掩盖,每一息,他眼底里的冷冽与嘲弄都比上一息更浓烈。 没来由的,孟韶欢心底里一寒。 管家嬷嬷去外面寻伞了,屋里就他们两个,恰逢屋外狂风大作,木窗未曾插上铁栓,被狂风拍的哗哗的飞动,几缕狂风吹进来,将屋舍内的灯吹灭了大半,刹那间,屋内暗的只有几星烛火。 在这一片昏暗之中,孟韶欢看不清裴琨玉的面了,那些烛火只能照亮他的轮廓,他的影狰狞的随着烛火的光芒左右摇晃,像是一匹即将扑杀过来的恶狼。 孟韶欢听见这匹恶狼极轻的笑了一声。 “殿下。”他道:“裴某给过您机会。” 他的尾调堪称轻快,甚至隐隐带着几分愉悦,在这房间散开的时候,却莫名的带出一股森森寒意,直顺着孟韶欢的脊梁窜起来。 孟韶欢突然记起来之前裴琨玉受全贵公公胁迫,离开前厅前时,侧过头与她说“尚有回路”的事。 裴琨玉竟是还没死心吗?他非要与她纠缠到天荒地老吗?管家嬷嬷怎么还不回来? 她一时心慌,下意识的向后退,却忘了自己身后有个蒲团,被绊了一瞬,险些倒下去,她好不容易站稳、压下了嗓子眼儿里那一声冒出来的惊叫后,强撑着公主的皮道:“本宫听不懂你的话,本宫是公主,你胆敢冒犯,本宫要上告皇兄!” 她是被逼急了,明知道自己不受元嘉帝待见,还敢管元嘉帝叫皇兄,扯着元嘉帝的虎皮来吓唬人。 但裴琨玉没有被吓到。 那高大的公子静默的站在一片昏暗中,不发一言地看着孟韶欢。 孟韶欢怕了,她忙不迭的爬起来往外跑,裴琨玉也不拦着她,她从他身边经过,冲到书房外,冲向厢房外。 她冲出去的时候,屋外正是瓢泼大雨,她一推开门,便看见管家嬷嬷被一个大理寺的官员摁倒在地,而另一旁还站着一个官员,一脸杀气腾腾的看着孟韶欢,厉声喊道:“启禀裴大人,属下方才在贼人全贵的房中搜到了北倭人的令牌与信件,这全贵通敌卖国!意在袭杀南陈使臣,挑动两国争端!” 孟韶欢迎面碰见这么一群人,心底里狠狠地抽了两下,正慌乱着,那位官员的刀尖突然对准了她。 “属下还在全贵房中搜到了些许物证,竟有几份是伪造出来的公主的牙牌身份,这公主——是假的!兴许也是全贵公公通敌卖国的一棋子!” 说话间,那些属下掏出来几份伪造的、印着官印的纸,向裴琨玉送过来。 这一声喊下来,雨幕中又是“轰隆”一声雷响,孟韶欢站在门边,只觉得眼前一阵发晕。 完蛋了。 掺和上通敌叛国,本来就是死罪,谁沾染了都要被削掉半条命,这事本来还可以解释,但是若是再掏出来她假公主的身份,她就算是没罪,也变成有罪了!怪不得这些人敢拿刀指着她,就算是现在她死在这,也不会有人为她叫一句屈! 而在她身后,那位裴大人的声音淡淡传来:“全国搜捕全贵,将全贵手下的人都审一遍,三个时辰后拿证词来见我,这位公主真假难辨——先押入屋内,关严,待本官回来后,由本官亲审,公主府继续封锁,案件所有细节对外保密,案件未曾水落石出之前,若泄出去一丝,仔细你们的舌头。” 孟韶欢打着颤,一点一点回过头去看他。 她突兀的意识到,现在裴琨玉已经借着局势,彻底抓牢了她了。 裴琨玉站在昏暗的书房中,身后是无穷无尽的、粘稠的黑幕,而他,接过属下送来的物证后,静静地看着浑身发软的羔羊,裂开森森的白牙,披着一张人皮,有理有据的唤她。 “公主。”他道:“劳您归房,待裴某忙完,再回来问您些话。” 若叫旁人见了,定会觉得这位大人临危不惧,行事有度,哪怕这公主身份有疑惑,他也不曾冒犯,但这落到孟韶欢眼里,就相当于一头豺狼在请她入瓮。 孟韶欢不敢进去。 她死死地抓着木槅门,一句辩驳的话都说不出,只白着脸,一步一步往后退,一双眼中满是惊惧。 她想到了更多。 当初裴琨玉说会将她从李霆云身边带走,讨要不成之后,直接假扮水匪将她抢走——这就不是寻常人能想出来的办法。 而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甚至天真的以为一个全贵能压得住他,她沉溺在了全贵钩织出来的美梦里,完全忘了裴琨玉这个人的手段。 他骨子里就藏着几分不择手段的凶狠,只是被裴氏一直压着,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,但是真发起疯来,连李霆云那么个人都要退避三舍,偏孟韶欢总记着他对她的纵容,在心里将他的危险一压在压,直到,直到今日—— 全贵跑了,南陈使臣死了,她的身份摇摇欲坠,天大的罪压下来,刚飞上枝头的凤凰被人抓着尾巴薅下来,连一声尖叫都喊不出来。 她的脑袋里冒出来了个更骇人的想法。 那南陈使臣,真是全贵杀的吗? 一个只知道睡几个女人的烂货,平日里只会弄权,跟裴琨玉对峙都要搞出来十几个太监围着,这样的胆量,真的有那个本事去做什么细作吗?又真的有能耐杀了南陈使臣吗? 那不是全贵,还能是谁呢? 脸蛋苍白的公主似是想到了什么关键,整个人突兀的打了个颤,竟是头都不敢抬,也不敢看裴琨玉的脸,只一步一步往后退,似是想逃离这一处书房。 离他远一点! 他疯了!这样大的罪,这样骇人的事,这可比当初裴老大人冤枉下属的罪要重的多!裴老大人那件事顶多全家流放,这件事若是翻出来,九族都要被砍,被圣上发现,整个裴氏都要完蛋,他拿上百条、不,上千条人命在发疯! 就为了报复她一通,恶狠狠地将她踩下来吗?这值得吗? 她又想,他连自己的家族都可以拿来赌,又何况是她? 她落到他的手里,又能有什么活路? 她得跑。 可偏生,她身后是对裴琨玉唯命是从的大理寺官员,这些官员们将裴琨玉的话奉为圣旨,见这位身份存疑的公主竟然敢往后退,一旁的官员便上前,暗藏了几分力道,以刀鞘拍在她的后背上! 这一下力道太重,孟韶欢向前踉跄着扑倒,竟是正好扑倒在裴琨玉的面前,于此同时,她身后的大理寺官员冲进来,直接拿着一截绳子把她给捆了! 大理寺官员捆她的时候,还心想,这都算客气的了,若是落到北典府司的手里,估计这会儿都抽上鞭子问刑了! 官员将孟韶欢捆起来时,裴琨玉目不斜视的走出了这书房中,去处理旁的事了。 孟韶欢则被捆住手脚,丢进了书房中。 书房昏暗,她一个人在其中,根本无法动作,只能在地面上匍匐着爬两下,但她实在是高估了她这一身皮肉,她不过是动弹两下,便觉得手腕脚腕处火辣辣的疼。 门口看守留下了两位,其中一位官员见她扑腾的厉害,还阴恻恻的道了一句:“再折腾,别怪本官无礼了。” 这是已经将她当成假的来待了! 孟韶欢便不敢再动了,只匍匐在地上等。 这一等,就是一个时辰。 一个时辰之后,窗外呼啸的狂风暴雨都已经停了,裴琨玉捧着一个盒子,踩着湿漉漉的石板砖重新回到此处。 裴琨玉到后,便命这两个官员离开。 门外的两个官员离开、走远的时候,似乎又有人问:“就把大人一个人留下——他对付的过来么?那可能是细作探子啊!” 便有另一人发笑:“当大理寺没见过探子么?大人是大理寺少卿,审过的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,莫慌,她逃不出去的。” 就真如那大理寺的官员所说,随着木门“咔哒”一声关上,孟韶欢便再无路可逃了。 黑暗如同潮水一般涌上来,让孟韶欢心里打抖。 不行,她不能跟这么一个疯子在一个屋子里! 她应该起身逃跑,门跑不出去,但是内间窗户却是开着的,她有手有脚,还翻不出吗?别管她能跑多远了,就算是一头撞死都比落到裴琨玉手里好,但是,但她手脚都被束着,只能这么咬着牙忍着。 她只能匍匐在地上,看着裴琨玉一点一点走过来。 那清隽雅致的公子手里拿着一根蜡,蜡烛的光芒盈盈的照着四周,也照着地面上孟韶欢那双慌乱的眼。 裴琨玉饶有兴致的看了一会儿。 她被丢在了茶案旁边,正临着烧煮的茶具,因为手脚不通血,身子都显得格外僵硬,看他的时候,还因为手臂束后而无法坐起来。 方才还高高在上的公主,不过转息间,便被押入了房中,成了一个被关押的囚徒,只能在此瑟瑟发抖的趴着,等待他的审问。 他需要好好审问,茶总是小火煮透了的更清香些,此事急了,就品不到回甘,所以裴琨玉没有急着去收拾孟韶欢,而是站起身来,先将被风雨拍打的撞颤的窗户插销插上,后又将书房里的烛火一根一根的点起来。 书房里的烛火用的是缠枝花灯——这种灯颇为讲究,就是以金丝细细的盘绕成一颗比人还高的花树,花树的枝丫上摆满了各种烛台,其上插着蜡烛,一但被点燃起来,便是一颗火树。 这树还极其精雅漂亮,一颗缠枝花灯,能将整个厢房都照亮,孟韶欢的书房中足足有三颗。 门窗皆闭,风雨便被隔绝在了外面,只有隐隐的风声呼啸,倒显得这屋子内安静,烛火一被点起来,明亮的、温暖的火光便填满了整个书房,裴琨玉点好了最后一支蜡烛、回过身的时候,便见孟韶欢在跟身上的绳子较劲。 她试图把这身上的绳子拗断,然后将自己锁在上面的手脚放出来,但这绳子底下是大理寺特制的,大理寺的工匠艺技巧夺天工出神入化,她不过是白费功夫。 裴琨玉回头的时候,她正在努力的咬着牙用身子去撑绳子,察觉到裴琨玉的目光,她的动作一僵,那紧绷着的身子木在了原地,连脑袋都不敢抬了。 裴琨玉要怎么发落她呢?她干巴巴的咽了口唾沫。 她没见过男人发怒,但是思来应该都是一般的,她以前在乡间见过那些挥舞着沙包大的拳头上来打人的丈夫,将妻子打个半死发泄,换到高门大户,兴许是会体面一点,如李霆云一般,掐着她的脖颈逼她跪地求饶。 但是,裴琨玉却和他们都不一样。 裴琨玉没发怒。 他平静的走到了她的面前,声线平和道:“方才臣去查全贵的东西时,查到了一些关于朝政的事情,全贵一直在与东倭一族暗中往来,公主可知晓?” 孟韶欢不知晓,她什么都不知晓,那张面具下的面白了又青,却连一个字节都吐不出来。 “公主不肯说吗?”他的声音里似是带了几分遗憾:“既如此,裴某只能上刑了。” 孟韶欢倒在地上,心想,她哪里是不肯说,她是不知道! 而裴琨玉也一定知道她不知道,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细作,但裴琨玉偏要将她当成细作来一道审问。 “公主来京中时辰尚短,大概不知道京中的刑罚规矩。” 那月白风清的公子缓缓跪坐到她的面前,抬起手,伸向了她身上的绳索,在孟韶欢惊讶的目光之中解开,随后,他从袖口中掏出一根银链子,系在了她的——足腕间。 孟韶欢几乎愣住了。 这是什么刑罚? 京中有这种刑罚? 她迟疑着向后躲,却被裴琨玉一把抓住了足腕。 他静默的跪坐在原地,只用一只手,就抓着孟韶欢的足腕硬生生将孟韶欢拖到了他的身前。 盈盈的烛火中,男人强健的腕,女人打颤的腿骨,像是一副旖旎的画。 “你——”被拖过来的孟韶欢贴着坚硬的、光可见人的地板,面颊都微微涨红,她终于发了声,声音也嘶哑发颤,问他:“你想做什么。” 这么大费周章的折腾,你想做什么呢? 裴琨玉不回应。 他生而内敛,不肯说“爱”,哪怕是在床笫间最动情的时候,也说不出来一句“我爱你”、“我离不开你”,现在更不肯说恨,好像一旦说了“我恨你”、“我要报复你”,就承认了自己忘不掉那段情,凭空矮了一截似得,他也不会骂人,也不会说出来什么讥诮的、讽刺的话,只会按部就班,一步一步,将计划扭到他想要的方向去。 就像是现在。 不管孟韶欢说什么,做什么,他都只按着他自己的话继续说。 “原本在大奉,男女都是同刑,每每遇到大案,男人要剖开肚皮,掂一掂骨头有多重,女人也是如此。” “犯了法,就都是罪人,罪人,就不分男女。” “只是先帝慈悲,不忍见此,便曾下命,不允刑上官妇女子,不可见外伤。” 他将手上的盒子“咔嚓”一声打开了。 孟韶欢瞬间感受到了寒凉之气逸散而出,她的目光才落过去,那霁月风光的公子便将这盒子拜访在了她的面前,似是想让她看清楚这是什么。 “先帝有命,便再也不敢有人上刑,只是这罪妇也不能就此放过不审,便想了个折中的法子,一直沿用至今。” 孟韶欢正看见那盒子。 木盒子里面摆了三块大小不一的坚冰,显然是刚取出来的,也不知道要作何用。 她的念头才刚窜起来,就听见裴琨玉声线平和,继续道:“便是将女子衣裳扒净,将此物置于女子身下,不消片刻,便会痛彻心扉,取出来后,不留伤痕。” 这一句句落到孟韶欢耳朵里,如同一声声闷雷,全都炸到了孟韶欢的脑子里。 这种糟践人刑罚,哪里是人能受得住的?真要是落到身上,就算是不死,那也活不成啊! 她便说,裴琨玉不会这么容易放过她的!他好不容易抓住她,一定要好生折辱才能痛快,偏他这人做事滴水不漏,这么一个局天衣无缝。 和裴琨玉比起来,李霆云那个狗东西竟也显得眉清目秀了,最起码李霆云想不出来这么多恶心人的招数! 那纤细的、柔弱的姑娘似是很想骂人,但是却又一句都骂不出来,只能抖着,一步步往后退,然后又被人握着足腕抓回来,她抬腿去踢,被扒下珍珠履与亵裤,他的手那样宽,用力一压,像是要把孟韶欢压碎了。 公主的华丽衣裳被扒下了一半,露出了白嫩的腿,粉嫩的足,娇娇的肌肤随着她的踢打而颤抖,满室烛火盈盈如水的亮着,照着她羊羔一样的肌肤。 “裴公子——”孟韶欢被吓坏了,她屈服了,她认清了这个形式,她知道裴琨玉这样欺辱她,是怨恨她中途弃他而去,所以她决定再拿出来自己当初那一套颠倒黑白的本事,一开口眼泪便先流下来,她哀哀的道:“我当日...我当日是想去找裴公子的,只是路上因那玉佩漏了行踪,被全贵抓住了,后又受了全贵的胁迫,他说我不当公主便杀了我,也不允我认旁人,我只能当做不认识你,我不是不想认你,我只是害怕,这老太监颇为厉害,他——” 孟韶欢的话还没说完,裴琨玉便重重的捏了她的腿骨。 她哭的那样惨,说的那样可怜,听起来也都是真话,落到裴琨玉耳朵里,激起了一片说不出的燥意与恨意。 不肯认我,还是不想认我? 这老太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控住你,叫你一句话都传不出吗? 你当初为了我,肯撞墙而亡,那一日为何不肯从暗室里面撞出来呢? 是真的受了全贵的胁迫,还是心底里也对南陈的权势生出了渴望? 他不知道。 裴琨玉不肯听她继续说那些话,他怕自己会动摇,他分不清孟韶欢这些是真话还是假话,他痛,他哀,他悲,他恨,他怨,他被折磨了太久,所以他不肯放过她。 “裴某听不懂。”那如月光清寒的公子垂下黑如鸦羽的睫,一字一顿道:“裴某与公主先前,从不相识,何来报复?现下所为,不过查案而已。” 他今日,是一定要对她上刑的。 她不认他,她与全贵同流合污,她想着去南陈嫁一个皇子,那他就要让她尝尝背叛的惩罚。 裴琨玉抬手,从盒子中,捡起了一块坚冰。 |